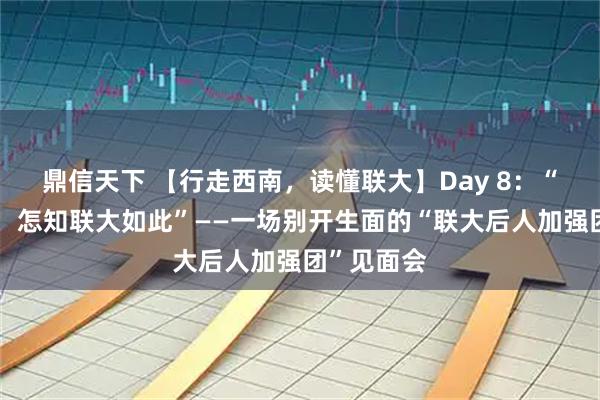
作者:南开河南校友会副会长 时文君鼎信天下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放下麦克风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昆曲《牡丹亭》的这句戏文。但我想对台下的观众说的是,“不走西南,怎知联大如此”!
“重走”第八天,在重温了西南联大入校仪式后,毅行团举行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经由西南联大教务长郑天挺之孙郑光牵头,在南开北京校友会会长刘亦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荣幸地邀请到郑光、朱自清之孙朱小涛、梁思成林徽因之孙梁鉴、郑振铎之孙郑源、王云亭外孙女王菁、徐旭生之孙徐十周等先贤后代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也就是云南师范大学,与毅行团的111名团员面对面进行交流。
而我有幸成为这场见面会的主持人。对我们而言,郑天挺、朱自清、郑振铎、梁思成、林徽因、周培源几位先生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唯有研究历史与考古的徐旭生先生,因年代稍远,我们对他略感生疏。这几位抗战时期文化、教育领域的学者大师要么在西南联大教书,要么与联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能带领大家与这几位大师的后人见面,我内心满是激动。
展开剩余86%为做好访谈,活动前我专门在酒店拜访了几位先生,向他们请教祖辈的往事。几位先生虽已六七十岁,却精神矍铄。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身形都很高大,待人更是谦和。面对我这样的后辈,自然又开心地分享祖辈故事——这份交流让我心里有了底,第二天的主持也变得游刃有余、流畅自如。
见面会上,毅行团中来自南开、北大、清华的校友分别向五位先生提问。
第一位提问者是南开校友廉雪冬鼎信天下,她向朱小涛先生问及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清贫生活。
朱先生坦言,书中记载的清贫都是真的,朱自清先生还是西南联大“三大怪”之一:因生活贫寒、无衣御寒,常披着毛毡当作披风御寒。另外两“怪”分别是潘光旦的鹿皮背心和冯友兰的八卦包袱皮。这“三大怪”是抗战时期联大师生艰苦办学的生动写照。那时的朱自清先生,不仅要在特殊时期自己学补袜子,还在清贫中坚持完成了大量作品的创作,是“外表斯文扫地,内心风骨犹存”。抗战八年,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却是朱自清先生学术成果最多,写作最为勤奋的一段时期,平均下来,一年能完成两本书,包括《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国文教学》《伦敦杂记》等等。
第二位提问者是北大学长何世强,他向郑源先生请教了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抢救古籍的往事。今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人大文学院吴真教授的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以9.4的豆瓣高分引发关注,书中便聚焦了这段历史。
郑源先生特别介绍了吴真教授的研究。为还原史实,吴教授不仅遍访国内档案馆、图书馆,还专门赴台湾、日本挖掘馆藏资料,耗时十五年钩沉出这场“文化暗战”的诸多细节。抗战时上海沦陷,日军成立专门机构系统性掠夺古籍,甚至有日本特务多次围堵郑振铎,同时美英“友邦”与汉奸书商也在趁火打劫,一场“文化灭绝”浩劫正在上演。为阻止“史在他邦,文归海外”,郑振铎牵头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旧书店为据点网罗珍本,一面用民族情感说服竞争者,一面争取资金与日方竞价,甚至卖尽私藏维持工作。
“祖父在日记里写,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上了日军‘梅机关’的黑名单,却始终没有退却”,郑源先生说。抗战最后四年,郑振铎隐姓埋名独居,每天只吃一顿饭,托人将三千多种珍品古籍伪装成邮包送抵香港暂存,最终累计抢救善本达4.8万册,其中3万余册在他的守护下熬过战乱。即便曾因经费匮乏、友人误解受尽委屈,他心中“为后人留住文脉”的信念从未动摇,用一介书生的坚守,在敌战区筑起了一道文化防线。
第三个问题由南开的学长高凤勇向梁鉴先生提出。他既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孙,也是周培源的外孙。学长好奇,梁先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与人生选择。
梁鉴先生笑着回忆,自己童年时主要与外祖父周培源生活在一起,外祖父在西南联大时的往事,是家里常提起的“趣话”:那时昆明物价高昂,因为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周培源住在离学校有四十里之遥的地方。距离远,他便每天骑马去学校授课,但从未迟到,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周大将军”,成为一道独特的校园风景。周培源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跟随爱因斯坦做了一学年的广义相对论研究。学成归国后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从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和流体力学的研究工作,为物理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
同时,梁家的学术基因也深深影响着他。梁鉴先生提到,祖父梁思成和同事当年发现应县木塔后,一周内完成精准测量,为这座“中国古建瑰宝”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如今,他正沿着祖辈的足迹,整理出版关于应县木塔的详尽画册,希望延续这份对古建的守护。
第四个问题来自清华学姐孟艳军,她向郑光先生请教,作为西南联大总务长、同时也是优秀历史学家的郑天挺先生,为什么要牺牲大量专业时间投身校务管理?郑光先生对祖父的印象是什么?
郑光先生始终保持着谦逊,他平静地回应:祖父本有清晰的学术研究目标,但当学校提出希望他承担总务工作时,他还是选择挺身而出。在祖父看来,总务工作关系到整个联大的正常运转与发展,这份价值远胜于个人的学术追求。为此做出学术成就上的牺牲,是值得的。尽管郑光先生没有过多夸赞祖父的功绩,但言语间难掩对祖父“以校为先、甘于奉献”的崇敬之情,那份敬佩自然流露,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
作为主持人,我获得了最后一个提问的宝贵机会,对象是徐旭生之孙徐十周先生。这份提问源于一份特殊的情结:我是河南人,而徐旭生先生出生于河南南阳,是我的老乡;更重要的是,徐旭生先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50年代发现了洛阳二里头文化旧址,为夏文化研究奠定关键基础。作为河南人,我对中原的历史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特别想了解徐旭生先生的研究。
我专门请教了两个问题:一是1927年徐旭生先生发起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相关情况,二是抗战时期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的发展历程。
徐十周先生耐心解答,祖父徐旭生在几位爷爷辈里是最年长的,是郑天挺和朱自清的老师。他是中国现代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913年赴巴黎大学攻读哲学,1919年归国后历任北大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谈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徐先生格外自豪。1927年,祖父担任中方团长,力促双方签订对等合作的科考协议,彻底结束了此前外国团队随意窃取中国文物的历史,这场从1927年持续至1935年的考察(徐旭生参与到1929年),更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研究院先迁到南京,与中央研究院合并组建国立中研院,之后部分机构辗转至昆明,其中史学所在昆明坚守了八年;而祖父在1932年还曾以北平研究院史学所研究员的身份,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这项工作被誉为“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之作”。
徐先生还坦诚分享,自己并未延续祖父的考古研究,而是选择了物理学领域,后来还参与过国家相关研究的高端项目。但即便领域不同,他对祖父的学术精神与人生选择始终充满敬佩。
几位先生真诚分享,娓娓道来,这份情感让毅行团团员深受感动。这场面对面的对话,已不止是一次生动的交流,更像是一次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再次看到“弦歌不辍”的力量。
作者简介
时文君:南开大学旅游学系91届毕业生,南开河南校友会副会长。资深媒体人,高级国企品宣师,职业生涯中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译制节目奖、河南省新闻奖等重要行业大奖,具有丰富的新闻传播及外事工作经验,2018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做访问学者。
来源:南开北京校友会鼎信天下
发布于:天津市天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